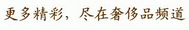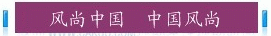-
台湾:一个处处有故事的地方
- 发布: 2008-5-06 00:00 来源:
《小康》杂志
文字: 大 |
中 |
小
我们接触的志工有退休的政府职员和教师,也有中青年知识者,他们或幽默风趣,或引经据典,或言简意赅,脾气个个好。参观传艺中心的展示馆时,正逢东南亚的民间乐器展,泰国、缅甸、菲律宾、越南诸国奇形怪状的丝竹管弦陈列两厢。老志工击打着一架竹制的乐器样品,随着音节跳荡,慢悠悠一语道破:“东方的打击乐器是演奏旋律的,西方的打击乐器则是确定节奏的。”参观了文昌庙,又转到庙对面的露天戏台,我们困惑于它何以如此之高,老志工有解:“按照古制,庙前戏台是演戏给庙里的神看的,人看戏是借了神的光,所以你看,这戏台和文昌帝君的底座一样高呢。”
志工们无偿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未必希求回报,但是每个城市的“志工银行”却确立了互助和回报的机制——你为社会所做的奉献都记载在“银行账号”里,待你年老体衰或需要任何帮助时,会得到相应的照顾。这样便形成一个既鼓励奉献美德又保障生存安全感的心理和现实机制:现在的受助者会因过去曾经助人而心安;现在的助人者亦可免于未来灯尽油枯之虞,放手做去。城市,因这些无处不在的志工身影而温暖多情。
随处可见的露天演出也散发着城市的温情。在高雄历史博物馆前,我看到了如雷贯耳的古典布袋戏,台前观众二三百,津津有味地看着,也许这是让传统戏曲免于衰亡的一个重要手段吧。文艺演出、文化场馆的门票都很便宜。台北故宫的门票100台币,相当于25元人民币,而台湾人平均薪水却相当于大陆人的2-3倍。故宫所藏甚丰,有定期轮展制度,不时更换新的展品。不单是外地游客,台北人自己也会常到这里观赏更新的展品。文化消费的低廉,使台湾的城市处处皆有文化生活,市民知识因此而日进。
当然,城市文化也不能全由普及性文化构成,一个城市的精神活力,主要靠创造性的、不安份的文化点燃,尽管这样的文化是缺少商业竞争力的。现任台北文化局长廖咸浩博士有一个颇为精辟的观点:在商业社会中,政府的角色应是制衡市场,扶植弱势文化。所谓“弱势文化”乃是和主流商业文化相对而言,尤指超越大众、曲高和寡、因而难见经济效益的高雅、前卫、小众的创造性文化。政府如果不拿出资金和空间扶植它们,任其在商业浪潮中自生自灭,那将是失职的。台北诸多富于创造力的文艺团体——大到声名赫赫的云门舞集,小到专做前卫戏剧的牯岭街小剧场,都受到文化局不附带任何要求的资金扶助。探索性艺术在此受到鼓励,比如以奖掖艺术电影为宗旨的台北电影节,现在的风头已堪与商业性的“金马奖”电影节相抗。创造性文化乃是城市的灵魂,对它尊重、呵护和扶持的程度,衡量着城市管理者的理性。
有趣的是,我所见到的各市县文化局长,无一例外都是学者,下属官员也学者居多,同时在大学兼课——这,大概是台北首任文化局长龙应台创下的范例。这些学者深知文化如同有机生命,乃人类灵魂之所系,亦明了文化发生成长之系统、发展所需之环境,因此不免把自身的行政工作,当作扶助文化有机生长、践行人文主义理念的契机。他们的工作态度是文化本位的,工作设置以系统思想为指针,力求科学性和人文性兼备,又有独立的行事权,不受上级行政干预,因此极大规避了文化行政化的武断粗暴之弊。这种现象,既似中国的文人从政传统之复活,又像西式专家政治的华文版,着实耐人寻味。
-

- 编辑:阿荣
来源: 《小康》杂志
-
- 奢华
- 珠宝
- 美容
- 服饰
- 女人
-
- 【私人专属定制】极度奢华庞巴迪Ca.
- 【奢侈品展推荐】Top Marques澳门超.
- 格拉苏蒂PanoMaticLunar XL系列男款.
- 品鉴“艾米龙”人文内涵 焕发流光溢.
- 【庞巴迪三轮摩托】庞巴迪Can-Am S.
- “智”动蓉城,“车”耀天府——第.
- 透过艾米龙热销,看中国的奢侈品消费
- G-SHOCK GD-100NS-7合作版活力无限
- 飞亚达与你一起“窃听”时间艺术之美
- 劳斯莱斯推出中国龙年特别系列 限量.
- 缅甸首届翡翠公盘 3亿天价拍得翡翠.
- 每克拉美 品质与服务并重_首家量贩.
- 粉红钻石首现网购市场 走秀网震撼推.
- 时尚先导许舜英:DERAIN钻饰引领兔.
- 中华之艺,艺显鹏城——中艺(香港.
- 世界上最大夜明珠亮相海南文昌 价值.
- 钻石小鸟巨献“旋.爱”炫亮王菲201.
- Gucci精美首饰Icon系列:演绎钻石印记
- 富御珠宝 推出花语恋翡翠镶钻系列
- 富御珠宝新翠葫芦翡翠胸坠 完美诠释.
- 纪念版“戛纳风情”的香水 戛纳电影.
- 丝蒂芙尼——新娘必备的护肤首选
- 不让疲倦在脸上留痕 巴黎欧莱雅男士.
- MISSHA谜尚BB家族,演绎均衡、柔美.
- 10年专注,开启美肌奇迹之旅——欧.
- 四款爱马仕Hermes屋顶花园系列淡香氛
- 雅诗兰黛 打造肌肤美丽未来
- 百雀羚夺标2011快乐女声 唱响“中国.
- Vinistyle百万产品免邮大试用
- 【世界十大香水品牌】世界上着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