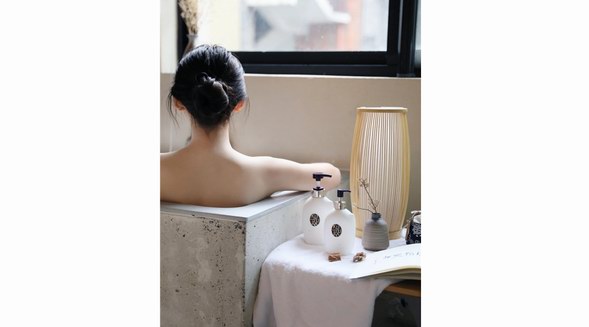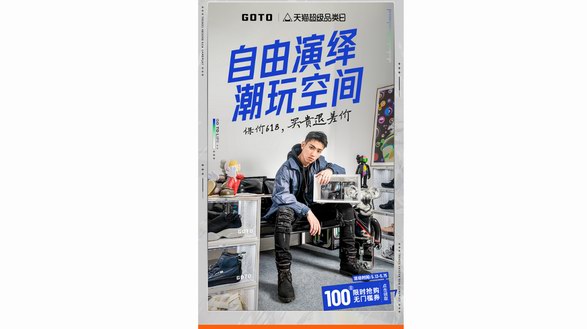作为工程巨鳄奥雅纳(Arup)在中国的一名主管,罗里麦格温(Rory McGowan)与某些世界一流的建筑师共同合作,在2008奥运建设期间重塑了北京的天际线。去年,当新项目的增长趋于稳定,他继续在蒙古、台湾、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展开工作。5年前,45岁的麦格温和他的俄罗斯太太瓦尔瓦拉沙妩若(Varvara Shavrova),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从伦敦移居北京。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发现,成功的工程解决方案根植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沟通,而这些人通常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政治视角以及商业动机。
2002年,奥雅纳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新总部项目竞标中胜出,中国的首都试图以一种惊人的高速建设这一标志性的全新建筑,于是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为了开发这一项目,我被迫对种种问题做出妥协。为了了解客户、技术顾问、决策者以及员工的诉求,我必须用心倾听,以获得他们的潜台词,以及充斥在我周围的各种议论。
在中国,项目会议以中英两种语言进行。
为期三年、每周两次向家庭教师学习普通话的经历,为我理解绝大多数讨论的主要内容打下了基础。
帮助新一代中国建筑师学会在过失中成长令人很有满足感。
上海的马达思班(Mada)以及北京的MAD和都市实践(Urbanus)建筑事务所的负责人都曾在国外工作和学习过,这使我们拥有了共同的参照点和设计语言。

设计、开发和建设需要花费5-10年时间
我有幸与当地商业伙伴建立了持久的友谊。葡萄牙的文化地标音乐厅(Casa da Música)用了8年时间建成。我们当地合作伙伴葡萄牙公司AFA的负责人鲁伊福塔多(Rui Furtado)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国之瑰宝。我特别欣赏由葡萄牙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设计的波诺瓦茶室(Boa Nova Tea House)和美妙的海鲜。
我的第一个志愿者项目是设计和建筑一座400英尺高的电缆高架通道,通往喀麦隆国家公园。
该项目工地与尼日利亚接壤,我们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合作,在伦敦设计了桥架。随后我离开伦敦,花了4个月时间,率领一个由志愿者和当地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完成了这个项目。学习如何激励志愿者,以及如何当好承包人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经历。我曾好几次回到这个公园开展其它工作。
1994年,我花了8个月时间在坦桑尼亚工作,为一位东非最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充当助手。
我们对该地区100万极度贫困人群的医疗需求进行了评估。这个项目使得工程建设回归其人性的一面。我最大的受益是认识到,为一个偏远村庄带去一口新的井或一所新的诊所的行动,与弄明白如何才能使之实现相比几乎不值一提。
1986年在布达佩斯理工大学(Budapest Technical University)实习期间,我认识到外国的真实现状常常与媒体报道有所出入。
当我想要兑换外币时,我会打开我的宿舍窗户宣布我的意向,而来自柬埔寨、古巴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的学生便会冒出来,向我提供极富竞争力的匈牙利福林兑换汇率。我靠着每周区区几个英磅的生活费用,一边享受城市里美妙的温泉浴(一种国家医疗体系的福利),一边啜着精美的托卡伊酒,活的就像个国王。
我和我的家人正在探索我们的下一趟国际之旅。
一旦我和我的公司就几个可能的地点列出清单,每个家庭成员便将开始投票。我妻子是一位艺术家,对于充满挑战和刺激的环境,和我有着同样的热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刚刚打开国门,她就离开了俄罗斯,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我们的孩子是带着对文化融合的期许开始他们的人生的。我们以爱尔兰神话英雄/异教徒和俄罗斯圣人的名字为菲昂亚历山大(Fionn Alexander)命名,而基里尔巴内帕特里克(Kirill Barney Patrick)的名字则来自创立了西里尔字母的僧侣。他们有时来我们在(爱尔兰)梅奥的度假小屋,和我们的大家庭一起过暑假。这使他们和爱尔兰之间建立起强大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