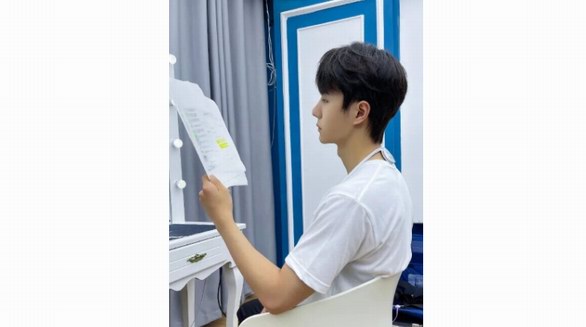曹保平:为观众交代真凶从哪里来
问:在一开场就把灭门案的经过放出来,是不是为了让观众尽快的进入故事?
曹保平:这个主要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观众不可能等到最后才知道谁是灭门的凶手。他们几个一出来,观众就会猜是不是他们。但是你要是不告诉观众,那还是有一个悬念,观众会一直猜,那到结尾的时候;你告诉观众就是他们,观众就会觉得没意思。因为你演半天才说凶手就是他们,那我早猜到是他们了。所以就一上来就告诉你,凶手就是他们。
那这样就带来第二个难题。小说是靠这个建立悬念的,那开始就说了谁是凶手,怎么到最后反转?就需要再重新建立。现在出现的第四个人物就是为了让观众最后的方向颠覆掉。
问:第四个人是怎么考虑的?原小说里完全没有。
曹保平: 原小说里有个问题,他们三个人是灭门的凶手,我接受不了,我觉得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它违背生活逻辑。如果他们三个是善良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灭一家五口,还把所有的痕迹收拾地干干净净,只留了一个指纹,这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下不了手,杀五个人跟杀鸡不一样,那个血光四溅,正常人是受不了的。这个说服不了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提不成立,那在电影里不能让这个前提继续下去。那就换成另外一个可能的前提。这三个人是混混,可能打架、杀人都干过,这次是阴差阳错在绝境下能下得去手。但是能下去手的前提是,这三个人从小长大就是混混,在社会上乱来的。但是要是这么设定在后面又说不清了。因为要是混混,他不可能杀了五口人以后就做好事赎罪。这个又不成立了。
邓超:像“小丑”希斯-莱杰一样体验角色
问:《烈日灼心》很虐心,你在演这部戏的过程中是什么状态?
邓超:把自己关起来,和角色待在一起,不出门,穿着小丰的衣服(那套协警服),然后到地摊上给小丰买内裤,穿在自己身上。那几个月就穿那些,不穿邓超的衣服,不穿邓超的内裤,不出去吃饭,不跟组里人说话。哦,拍戏间隙去了一趟《我是歌手》,当时一直拒绝海泉,我印象很深,他给我打电话,说“超儿,我们这有一个驻唱,你能不能过来”,我说我现在的状态完全没法去一个综艺节目。还去唱歌?又蹦又跳?后来海泉屡次打电话,我就去了两天,也是神经质,也是一次……
问:神游!跳脱了一下。
邓超:对,用的这个词很对。其实我厦门也有很多朋友,见面可以,但是不一起吃饭,因为我觉得小丰去不了那些地方。我也去了警局,体验一下协警是怎么工作的。协警是不能够配枪的,也不能配手铐,甚至衣服装备都是自己买的。包括怎么接活,因为你要跟着警察出去接活,你要是接好了,就能跟正式警察出个警,没有的话,那你就只能在那儿值班。然后给自己加了一个黄胶带,还有那个塑料的锁扣(用来绑手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备的装备。当然,外化的东西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跟小丰多住在一块儿,多去感受那种逃亡的感觉。就像我喜欢的“小丑”希斯-莱杰,他每拍一个戏,就会去一个旅馆,自己住七天,一直跟自己说话。
段奕宏:警察难演,要靠精神气质取胜
问:伊谷春这个角色是个警察,警察这个职业给人的惯性认知是某一种固定的形象,代表正义,代表国家公权力,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立体化,这会不会成为你接演《烈日灼心》的障碍?
段奕宏: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我从剧本上没有看到这个角色有别的可取之处,我很担心我呈现出来就只能是这样。当我作为观众去看一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我能呈现到什么程度?我能塑造成什么程度?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平平的,都见过。最开始我为什么拒绝(《烈日灼心》)呢?就是这个原因。警察这个职业我不熟悉,原剧本对这个职业的描述笔墨都是有限的,我就会想,这么一个有限笔墨的人物,就有可能代表导演的重心。如果篇幅有限,导演的精力又不在这儿,只是一个辅助角色的话,那就更没可能我们一起呈现出来一个不一样的警察形象。
问:后来你们是怎么讨论伊谷春这个角色的?
段奕宏:然后就聊啊。成全这个人物不能靠我一己之力,一定是大家都意识到了,这(电影)一定是几条腿走路。缺一条腿,你认为可以,那好吧,我肯定就不来了。你认为不可以,那行,至少说明你的态度在这儿,那咱们有机会。就像当年的元朗(《士兵突击》)一样,你认为很重,有什么措施吗?我们一起来创作。首先作为导演,你有这个态度,那么我在关键的时候有解读和创造的权力,我们一起来造就这个人物,那行。心里有这个踏实的感觉,我才接受了这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