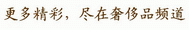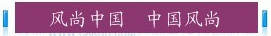-
歼-20简介:歼-20图片 歼-20参数 歼-20配置 中国歼20隐形战机首飞花絮视频
- 发布: 2011-1-16 10:35 来源:
风尚综合
文字: 大 |
中 |
小
歼20滑行试验图-:歼-20图片 歼-20参数 歼-20配置 歼20隐形战机首飞花絮
四代 DSI 恰好在这三个方面都用最小的折衷做到了。DSI 本来就是用来分离附面层的,DSI 的附面层分离效果好,阻力小,总压恢复好,但 DSI 只能对一个有限的速度范围优化,很难做到对很大的速度范围都高度有效。另外,DSI 的凸曲面设计本来就相当复杂,需要考虑三维流场和压力分布。为了隐身,四代的机头是菱形截面,进气口是像 V 形一样向两侧倾斜,在大迎角下流场更加复杂。为了改善大迎角下进气口对空气的“捕捉”效果,进气口像 F-15 一样带一点后掠。为了不给 DSI 设计带来太大的困扰,后掠没有 F-15 那么大。但 V 形机头下半部的前机身预压缩能力不足了进气口后掠不足的缺憾。另外,正因为进气口后掠,下唇位置靠后,所以凸曲面位置偏上,和凸曲面剖开造成两撇“胡须”的下一半的位置正好对上。
四代之前,所有隐身战斗机都采用固定进气口。固定进气口结构简单,没有可动部件,雷达反射特征小。从 F-22 开始,固定进气口几乎成为隐身战斗机的固有特征,F-35、T-50 都是固定进气口。但固定进气口只能对较小的马赫数范围优化,F-16 采用固定进气口之后,尽管推重比 F-104 增加了 40%,但最大速度相当,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F-16 的固定进气口是为跨音速格斗而不是最高速度而优化的,而 F-104 的进气口是可以通过半锥可调,所以在更大速度范围内保持最优。在超音速飞行时,进气口的唇口也造成激波,激波的锋面好比气帘,气流通过激波锋面的时候得到减速。可调进气口可以在不同速度下有效地控制激波的形状和位置,使气流达到发动机正面的时候为最优速度、最高压力。不可调进气口只能在设计速度做到这一点,在其他速度下,要么气流速度依然过高,发动机前面几级压缩机非但起不到压缩机的作用,反而变成风车,使气流减速到亚音速;或者速度过低,大大增加压缩机的负担。F22战斗机
F-22 采用加莱特进气口,也称双斜切双压缩面进气口,或者斜切菱形进气口,不同的说法,都是一个意思。这个设计比 DSI 超音速性能好,适应的速度范围更大,但毕竟还是固定进气口,最终逃不过固定进气口的限制。好在 F-22 有两台变态的发动机,超音速巡航没有问题。T-50 的超音速巡航性能现在不清楚,T-50 的进气口和 F-22 有所不同,但原理大致相似。F-35 采用 DSI,只有一台发动机,尽管推力变态,还是力不从心,最高速度只有 M1.6,超巡就免提了。四代要做到超巡,但中国没有 F-22 这样变态的发动机,只有用可调进气口来帮忙,达到足够的超巡性能。四代的进气口上唇可以下垂,像 F-15 一样,这就是可调进气口。和 F-15 不同的是,F-15 的可调进气口是暴露在外的,而四代的可调进气口是包拢在进气口结构内的。四代这样做当然是出于隐身的考虑,但可能造成进气口唇口较厚、阻力增加的问题。工程设计本来就是得失权衡的过程,只要最终结果得大于失,这就是值得的。不过四代的进气口上唇下垂如何避免和 DSI 的鼓包打架,这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有待更多的细节图片才能解惑。活动上唇和固定外壳之间不可避免的间隙里,如何避免杂物和尘土嵌进去,造成可调上唇动作受阻,这也是一个具体的工程问题。四代的进气口可算是 DSI、加莱特和 F-15 那样的可调锲形的结合体,这也给了四代正面大青蛙一样的特征。
有的示意图上,四代的鸭翼是箭形的,但从正面照片来看,鸭翼是梯形的。按照尽量减少边缘角度的 edge alighnment 原则,机翼形状应该和鸭翼一致,机翼、鸭翼前后缘对齐。如果最后证明鸭翼不是梯形而是箭形的,那也无妨,鸭翼和机翼的前后缘不一定需要左面对左面,左面对右面也是可以的。机翼采用 M 形或 W 形虽然也符合 edge alighnment 原则,但增加了内角和凸角,增加后向雷达反射特征,能避免最好避免,只有在前掠后缘导致翼根长于机体长度的时候才不得已而为之。双垂尾的形状估计了鸭翼一致,有利于边缘对齐。垂尾翼尖斜切一刀,估计机翼、鸭翼也有同样角度的斜切一刀。米格战斗机的垂尾经常有这么一刀,F-15 的翼尖也是这个样子,这是为了躲开翼尖涡流造成的额外阻力。
TAG: 歼-20参数 歼-20简介 歼-20配置 歼-20图片 歼20首飞 隐形战机 中国歼20
-
- 奢华
- 珠宝
- 美容
- 服饰
- 女人
-
- 【私人专属定制】极度奢华庞巴迪Ca.
- 【奢侈品展推荐】Top Marques澳门超.
- 格拉苏蒂PanoMaticLunar XL系列男款.
- 品鉴“艾米龙”人文内涵 焕发流光溢.
- 【庞巴迪三轮摩托】庞巴迪Can-Am S.
- “智”动蓉城,“车”耀天府——第.
- 透过艾米龙热销,看中国的奢侈品消费
- G-SHOCK GD-100NS-7合作版活力无限
- 飞亚达与你一起“窃听”时间艺术之美
- 劳斯莱斯推出中国龙年特别系列 限量.
- 缅甸首届翡翠公盘 3亿天价拍得翡翠.
- 每克拉美 品质与服务并重_首家量贩.
- 粉红钻石首现网购市场 走秀网震撼推.
- 时尚先导许舜英:DERAIN钻饰引领兔.
- 中华之艺,艺显鹏城——中艺(香港.
- 世界上最大夜明珠亮相海南文昌 价值.
- 钻石小鸟巨献“旋.爱”炫亮王菲201.
- Gucci精美首饰Icon系列:演绎钻石印记
- 富御珠宝 推出花语恋翡翠镶钻系列
- 富御珠宝新翠葫芦翡翠胸坠 完美诠释.
- 纪念版“戛纳风情”的香水 戛纳电影.
- 丝蒂芙尼——新娘必备的护肤首选
- 不让疲倦在脸上留痕 巴黎欧莱雅男士.
- MISSHA谜尚BB家族,演绎均衡、柔美.
- 10年专注,开启美肌奇迹之旅——欧.
- 四款爱马仕Hermes屋顶花园系列淡香氛
- 雅诗兰黛 打造肌肤美丽未来
- 百雀羚夺标2011快乐女声 唱响“中国.
- Vinistyle百万产品免邮大试用
- 【世界十大香水品牌】世界上着名的.